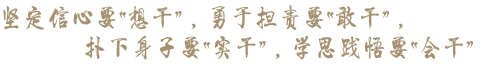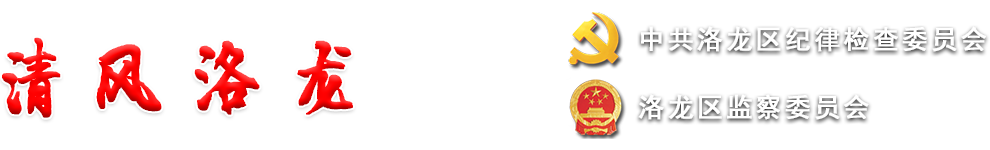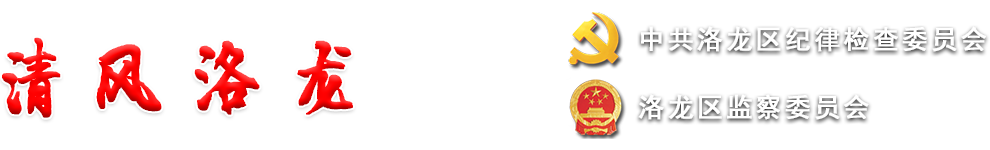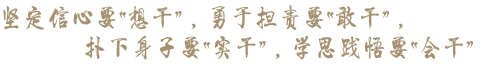我的父亲母亲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生人,和那时候很多农村人一样,他们的婚姻是指腹为婚。
姥爷和爷爷两家关系好。姥爷读过私塾,为人儒雅大气,在乡邻中极有声望。姥姥是温婉贤淑的贤内助,相夫教子,不遗余力。于是,在姥姥肚子里还怀着母亲的时候,爷爷就对姥爷说,此胎若还为女,就给我家老二当媳妇吧。姥爷姥姥也钦佩爷爷奶奶的为人,便应承下来。
姥姥在腊月二十四日产一女婴,正巧和父亲同月同日生。冥冥之中,好似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将两人紧紧联系在一起。
当父亲母亲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,爷爷家的光景已经不是很好。姥爷的亲戚就劝取消这门亲事,免得孩子将来受罪。但是,姥爷说:“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,男子汉大丈夫一诺千金,万不可坏了名声。”最后,母亲在二斗麦子、几尺布的“彩礼”下进了我家门。
母亲结婚后,爷爷奶奶手把手教母亲做饭、针线缝纫、待人接物等事情,让母亲感受到了一种温暖与关爱。后来,母亲对我说:“我在婆家享福了,你爷爷奶奶对我都很好!”母亲帮着爷爷奶奶把几个小叔子拉扯大,她和大家相处融洽,很受乡邻的赞赏和爷爷奶奶的青睐。
记忆中最难忘的是,母亲总是把好吃的东西让我们送给爷爷奶奶。看着我们很馋的样子,母亲语重心长地说:“你们还小,以后有的是好吃的。可爷爷奶奶年龄大了,牙口不好了,现在有好吃的要让他们吃……”母亲没有华丽的言语,每每只是用实际行动,表达着自己对老人的孝敬和感恩。我们姐弟从小看在眼里、学在心里,受益颇深。
父亲是一位煤矿工人,一辈子兢兢业业地工作,踏踏实实地做人。他讷言缓行,性情温和,诚实守信,不说三道四,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,从来不去和别人攀比,把日子过得平静有序。
母亲则是个急性子,嘴快、手快、脚勤,一天到晚嘴不停,手脚不闲,把家里打理得整整齐齐、一尘不染。她对我们提出了诸多“不许”,这对我们孩子来说无疑是最大的警戒。她要求我们:须把东西用完了放回原地;须把坐皱了的沙发布、床单仔细抚平;坐着的时候不能倾斜着身子,像没有骨头架子一样;不能抖腿或脚;不能拿别人东西,等等。我们稍一犯错误,母亲就摆出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气势。可以说,我们是在母亲的呵斥和约束中成长起来的。母亲在大声呵斥我们时,父亲会温温地来一句:“你声音小些,孩子都乖着呢!”母亲只说一句:“你就当老好人吧。”确实,曾经一段时间,我们都很喜欢父亲害怕母亲。
父亲不去求人办事。在我们上学和就业的关键时刻,父亲始终是一副四平八稳的样子。他认为,任何事情都应是自己辛勤劳动得来的,他看不惯那些为了个人利益钻营投机的人。初上班时,父亲一个月才拿几十元工资,过年回家,除了给母亲留几元零用钱,其余的全数上交爷爷。爷爷用父亲的钱和家庭其他微薄收入,支付一大家人的家庭开支。
母亲是一个心气很强的人,年轻时吃了很大的苦头,她作为家属,在煤矿的河滩砸过石头、编过铁丝网、给拉煤车上过煤,做的都是些苦力活,但是她毫无怨言,每天乐呵呵地生活,伺候父亲,照顾我们。在这样的家庭里,我们姐弟三人初长成人。而母亲的两鬓已经斑白,曾经苗条的腰肢已渐显臃肿,挺直的身板已经微驼,犀利的目光已经失去了往日的风采。我们也再没有听到她大声斥责我们时的气壮山河。不经意间我们收获了岁月的恩赐,却丢失了无法追回的亲人往昔。
我的父亲母亲用自己的爱和责任营造着一个健康温馨的家,他们的喜怒哀乐因我们的遭遇或起或伏,他们的感情世界因我们的存在更加绚丽多彩。他们一生孝敬长辈、呵护兄弟姐妹、抚育儿女子孙,他们一生何曾为自己真正活过一天?但他们确实用自身的行动为我们树立了做人的标尺。
父亲母亲是我生命的起源,是我永远无法舍弃的牵挂与爱恋。 |